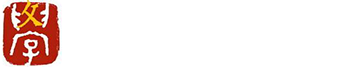本文原发于《文艺报》2020年4月20日6版
河畔书宴是bat365中国在线平台官方网站2019级汉语言文学基地班二班内部的读书会,2019年10月份由班主任唐诗人老师提议成立。读书会成员都是“00后”大学生,旨在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阅读文学经典。读书会尤其重视文学体验,成员之间分享最真实的文学阅读感受,同时也借助讨论更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和文学阅读的复杂性。这一期,老师带同学们阅读的作品是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
唐诗人:很多人一谈到读经典,就想起读西方名著和古代经典,可是我觉得这不够。读当代作品,我们会感受到文学与我们自身的关系,会理解文学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是一种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时代直接相关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感受到文学与自身关系的时候,才谈得上感兴趣和有价值。我很希望听到大家读这个小说时的真实感受,你们都是“00后”,你们的直观感受或许比你们从一些书本上所看到的解读和评价更有意思。
杨梓姗 杨
杨梓姗: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90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同驯鹿一起踩出一道道蜿蜒曲折的小路,在广袤森林中留下一点点人类的烟火气息。“我”见过太多的人,与他们同生共息最后又送走了他们。山外的世界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游牧生活也渐渐消失于现代化的滚滚轰鸣中,纵然生活早已千疮百孔,“我”仍静守这片山林,在亘古不变的苍翠中坐看云卷云舒。
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着眼于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鄂温克族人。作者并不避讳矛盾与冲突,正如月有阴晴圆缺才完整,通过这些人物和情节,我们更能看到一个完整的鄂温克民族,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在跋中提到的鄂温克人的直率。
有人将这本书归纳为生态文学,我认为这也是很有道理的。书中描写的生活与自然紧密相关,族人们受惠于自然,同样也感激它、尊重它。无论是捕到猎物后先供奉神灵,亦或是在死后选择风葬,都表现出这一民族对自然的敬畏。我猜不到鄂温克民族与山林河流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几百或是上千年?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在百年内迅速消逝,伐木机带走了苍天古树,也带走了鄂温克人熟悉的游牧生活。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进步”,在鄂温克人眼里是否会是“亵渎”或“叛逆”?我想作者的态度很明确,在小说的开头,“我”已坚定地说,“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除此之外,我想文中那神乎其神的萨满,同样也在警醒着我们。也许我们无法相信萨满们真有神奇的魔力,但在疑惑中我们也不免心惊,不禁重新思考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重审我们的地位与价值。
陈李涵
陈李涵:我读《额尔古纳河右岸》得到的最深切的思考,确实是关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看一个过着游猎生活的民族是如何与自然息息相关,又如何一步步远离自然,脱离自然,就好像看一部人类如何从敬畏自然走向征服自然的史书。早期的鄂温克族就是一个深深嵌入自然里的民族。他们以自然而生,朝夕相伴的都是天边的云彩和清澈的风,驯鹿是他们最亲密的挚友,连捕获的猎物也需为他们举行风葬。他们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也珍视敬重自然。
而自然赠予他们生存的同时,也让他们生活得纯粹美好。他们没有太多关于利益的考量,需要思考的,好像只有林间的雨和冬天的雪。但是,当现代文明的车轮滚滚而至,这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也被卷入其中。心灵为自然腾出的空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光怪陆离带来的浮躁和无尽烦恼。我想,初生赤子大概都有一颗向往山川湖海的心,但是钢筋楼房往往为他们的灵气筑起一座囚笼,使人眼前只见功名利禄,纸醉金迷。但自然不会,它只会像画师一样给心灵添上色彩,稚气未脱的孩童可以从自然的画作里满足好奇,成熟稳重的人可以从画作里找到智慧和深刻,绝不会让人感到迷茫和无措。
所以,《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探讨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冲击时,也关注一个原始民族初入城市生活无处安放的心灵。这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游牧、游猎民族所面临的难题,更是一个人类在面对工业文明时应该如何安定自己灵魂的重要问题。我想我在书中找到的答案是敬畏自然并且热爱自然。
高绪垚
高绪壵:我与陈李涵和杨梓珊有近似的感受,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不一样。《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小说带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先进的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正如作者在另一篇作品《土著的落日》中所说的:“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最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人!”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看老了。”开头这段话,是“我”的一句自叙,但我觉得这是鄂温克族千百年来历史的总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以地为伴,以天为友,雨和雪早已是他们的常客了,但是正如雨和雪因为工业污染而变得越来越稀少一样,鄂温克族也因为工业化文明的冲击而走向了没落,他们曾经拥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习俗和习惯,但这一切都在先进文化的冲击下而逐渐消失。小说中西班在被问到为什么要造字时回答道:“这么好听的话没有文字,是多么可惜呀。”一个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却没有相应的文字来记录和表达,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当那些知道这些事迹的老人们一位一位的相继死去,最后还有谁会记得这里曾经有一个民族有过如此瑰丽的文明呢?
林思仪
林思仪:书中更直击人心的,是作者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描写。以“我”在不同年龄的不同口吻,展示着鄂温克人的生命观。“如果是小鹿离开了,它还会把美丽的蹄印留在林地上,可是姐姐走得像侵蚀了她的风一样,只叫了那么一声,就无声无息了”。“月亮让我懂得了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我想起尼都萨满说列娜是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就觉得她是去了一个好地方,而不怕再想起她了”。从彷徨害怕到平静释然,让人对生命多了一份理解。
从故事的中段开始,作者就像搭了一座桥,每向前一步,就塌一块木板,持续灾难的情节让人心疼绝望。萨满这个角色是神秘而伟大的,他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符号,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神力,或许我们无法理解,但须敬畏,他肩负一个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萨满的妮浩不止一次牺牲自己的孩子而去拯救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他人。她无奈地将自己的孩子比作“别人的孩子”,可在选择的关头,她仍坚定地说可她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的孩子”还有活下去的可能,怎么能……每一次选择,都是牺牲她自己。让读者一次次为这个伟大的萨满和悲伤的母亲落泪。尽管距离遥远,但人世间最普遍的情感——小爱与大爱,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书里描写了很多人物。每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角,他们的性格都那么鲜活饱满,拥有纯粹却也复杂的情感。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理解每个人背后的故事,才能真正认识他们。
我在这里选择印象深刻的例子:伊芙琳与妮浩。伊芙琳因为妮浩没有嫁给自己的儿子而对妮浩怀恨在心。家庭悲剧让伊芙琳性格扭曲,开始用她尖酸刻薄的语言伤害每一个无辜的人。而等到伊芙琳的好友也是死对头玛丽亚死后,伊芙琳善良的心又回归了。她在生命的尽头为妮浩的儿子除去病痛。作者让清风驱散伊芙琳心中所有世俗的愤怒,让花朵作为食物洗净她肠中淤积的油腻,使她有一个安然而洁净的结局。也让我对人性本善有了欣慰的感受。
周钰杰
周钰杰:妮浩和作为叙述者的“我”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物。妮浩出场时还是二八年纪,孩子模样,对一切事物都是一窍不通。天有所指,萨满之重任落在了妮浩身上。可是万物都是守恒的,妮浩可以治愈消灾,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一命换一命。妮浩眼泪来不及抹去,意识已经被超自然事物占据,拯救素不相干的人,她亲爱的孩子们,被马蜂蜇死,被洪水卷走,胎死腹中,落荒而逃……人生在世,主动权不能时时握在手里,被责任义务钉死原地。额尔古纳河畔的人们,虔诚地信仰着我们所说的未知,保留着内心的纯粹和慷慨。“我”是雨雪的老人,是沉着的叙述者,是死亡的见证者。父亲坠于雷电,母亲落于舞蹈,丈夫败于自然,孩子们离去时自己已云鬓霜发……“我”是女人,但“我”不失韧性。统治者追求长盛不衰,平凡人活得太久了,亲人逐个离去,茕茕孑立时,剩下的是寂寞还是坚强?“我”叙述得很平静,但“我”内心早已覆满褶皱。
赵婷:小说的叙事方式别出心裁,作者把一个民族近百年兴衰灿烂的光阴浓缩到“我”短短90年的生命历程中,再把这九十载日日夜夜的光阴凝练到短短一天中,也就是这本书的四个部分:“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黄昏”、“尾声:半个月亮”。整个故事就像是一位老婆婆盘坐在床上,给你断断续续讲了一天她的人生。而她的人生,就是整个鄂温克族的缩影。看起来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拼凑起来,却是一部娓娓道来的史诗。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很“迟子建”。从小人物口中讲出的大历史,让这部民族史诗更真实、更自然。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的碑刻被飞扬的尘土掩埋,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风花雪月,却可以永不漫漶,雕镂人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日渐式微的传统文明?鄂温克人已经讲出了答案。就像他们在搬迁的时候总要把挖火塘和搭建希楞柱戳出的坑填平,再把垃圾清理在一起深埋,“让这样的地方不会因为我们住过而留下伤疤”一样,在被我们破坏的鄂温克人聚居地,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电锯、保护区搬离,让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会因为我们的造访而留下伤疤,让鄂温克文明不要因为我们的打扰而消失。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描写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弱小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挤压下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风情。本书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她表达了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等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额尔古纳河右岸》授奖词)